

1919年秋,陈焕镛只身前往海南岛,成为到此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

陈焕镛(中)在列宁格勒植物园。

1958年,陈焕镛(左二)与苏联科学家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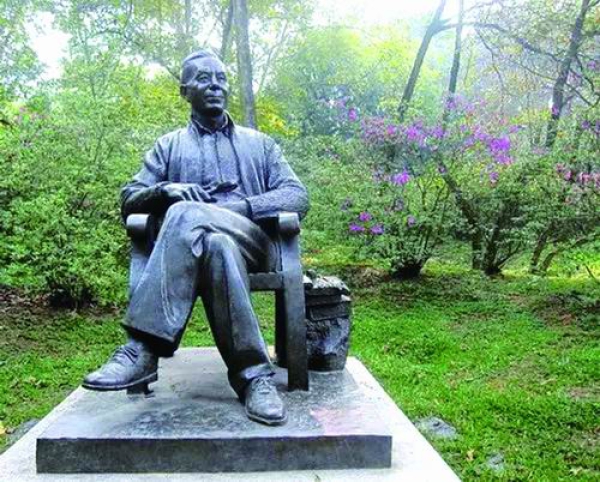
华南植物园的陈焕镛铜像
人物简介
陈焕镛(1890~1971),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深入研究华南植物区系,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其中银杉属为孑遗裸子植物,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科学意义;1954年被中科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并于次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创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他致力于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并在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搜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
人物生平
●1890年7月12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
●1909年,赴美国读书。
●1913年,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
●1915年,进入哈佛大学树木系。
●19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树木系,获得林学硕士学位,并以毕业论文优异获奖学金。同年,接受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1920年,担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教授。
●1921年,转至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至1927年)。
●1922年夏,与钱崇澍、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
●1924年,赴美国鉴定标本1年。
●1928年,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并在中山大学内建立起中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1933年,与钱崇澍、胡先骕等共同倡议创立中国植物学会,同年被选为学术评议员兼《中国植物学杂志》编辑。
●1935年,赴梧州创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并任所长,兼任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7年,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
●1959年,被聘任为《中国植物志》副主编,移居北京,主持这部中国植物分类学巨著的编纂工作。
●1971年1月18日,在广州逝世。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但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哈佛大学导师的挽留,放弃留在那里读博士的机会,回到生物学根基尚无的祖国,为我国植物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23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便因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曾被外国人大量采集、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各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各国出版的刊物而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并立下宏愿: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面貌。
自立下志愿那天起,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份初心的不悔践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陈焕镛出生于香港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才华横溢,曾创办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之一 ——《华字日报》,母亲则是古巴籍西班牙人。陈焕镛幼年时曾跟随父母回唐山,7岁移居上海,15岁前往广州,后来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读书。
陈焕镛本可选择另一种人生,但一颗中国心却不允许他置身事外。1913年,陈焕镛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树木系。1919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陈焕镛从美国归来,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那时,我们外出采集标本的条件很差。”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吴德邻曾前往云南采集标本,即便登上3000米的高山,身上也只是简单御寒的衣物,连雨衣雨鞋都没有。“而海南岛的条件比云南更艰苦。”吴德邻说。
那次原本计划为时一年的科考任务因陈焕镛的身体状况而被半途搁置。他先是被毒蜂蛰伤,之后又感染恶性疟疾,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
尽管身体虚弱,陈焕镛依然不忘携带已经采集好的标本,并将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码头。不幸的是,这些辛苦采集的标本被一场突发大火烧毁。
但他并未气馁。1922年夏,已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一年的陈焕镛与钱崇澍、秦仁昌共同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然而,这些标本与之前的标本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因存放地——东南大学“口字房”校舍起火而损毁。
连续遭遇打击的陈焕镛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征程,前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他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取得联系,与其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换得3万多份国外标本。
让植物学走得更远
1928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业学院任教时,基于与同事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交换的标本,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建立伊始,陈焕镛便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相媲美的设想。
为实现这一目标,陈焕镛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
“陈焕镛每次购买植物专著时都会买两本,一本被按照条目剪接,放在标本柜里,方便我们查阅;一本则作为资料留存,鉴定标本的准确性就提高了。”吴德邻说。
1954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陈焕镛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表示,至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当时居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陈焕镛院士在标本馆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馆藏已达百万号,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陈焕镛还特别重视植物学的应用,在他与秉志等生物学家的倡导下,于1956年建立了中国首批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管理格局沿用至今。上世纪60年代,他在研究植物的同时提出中国植物学者要加强植物资源利用研究。这种在研究基础上注重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早在1930年,陈焕镛就提出资源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等倡议。
此外,陈焕镛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专业图书馆。据1937年统计,馆藏中、西文图书达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杂志50种以上。许多珍贵的西方植物学文献均有收藏,如1753年出版的林奈的《植物种志》,以及欧美植物分类学的重要期刊和中国古农书、方志、本草等重要文献。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经典著作为后人开展植物学研究、编写植物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陈焕镛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对农林植物研究也倾力支持、慷慨解囊。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每年1000元大洋的补助费外,将基金会付给他的每年4000毫洋(广东、广西等地曾通行的货币)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设备费。
同时,陈焕镛也为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1958年春,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黄观程曾随陈焕镛到苏联考察和工作3个月,陈焕镛为那里的标本馆鉴定了一批尚未定名的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植物标本。
“外国学者对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钦佩之至。”黄观程在接受采访时说。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为了让中国植物学后继有人,陈焕镛不断帮助新人在学科上有所成就。吴德邻至今难忘,当年在研究所作为“小字辈”的自己如何在陈焕镛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兰花蕉科新科与新种的认定。
1962年,吴德邻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时,发现了两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一张采自广东信宜,一张采自海南保亭。后经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并且是两个新种,分别为兰花蕉和海南兰花蕉,其中兰花蕉现已被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濒危物种。
当吴德邻拿着标本向陈焕镛汇报时,陈焕镛还邀请北京植物所教授汪发缵帮其鉴定。确认无误后,吴德邻十分兴奋,准备立即发表相关论文。但陈焕镛却拦住了他:“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一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为了帮助吴德邻拿到国外的标本进行比较,陈焕镛当即写信给身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
“后来,陈所长又帮忙写信要了些外汇,寄给孙洪范,作为采集经费。我在不久后就收到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这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德邻回忆道。
在1963年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上,陈焕镛推举吴德邻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后来陈焕镛还亲自帮他修改英文摘要,并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更让吴德邻印象深刻的是,陈焕镛利用自己拉丁语的优势,在华南植物所开设拉丁语课的教学工作。“那个时候拉丁文是做植物分类学必修的语种,但国内会的人并不多。”吴德邻表示。陈焕镛还亲手制作了拉丁语卡片,帮助大家记忆。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曾在回忆陈焕镛时谈到,当年,像陈封怀、蒋英等第二代植物学家都是在陈焕镛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听导师陈封怀先生讲过,他们师生打成一片,一有空陈老就找他谈话,并经常请客。陈封怀先生自己成为植物学专家后,对导师始终非常尊敬。”
“良师”“益友”是许多人对陈焕镛的评价,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风,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求真精神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思想,永远值得后辈学习。
记者手记
“不忘初心”是时下听到最有担当的一句话。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陈焕镛一直全身心地诠释着这四个字。
陈焕镛为儿子取名“国仆”。陈国仆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称:“国仆二字,取精忠报国之意。”而陈焕镛自己也一直在践行这句话。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学校的标本和图书资料,陈焕镛先是把它们运到香港亲戚家中,后来又抱定“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决心,冲破重重阻碍,把标本和资料从日军的魔爪下取出并转运回国。
接受采访的吴德邻老先生已是86岁高龄,但他一直强调,自己在进入华南植物园时,与已经是所长的陈焕镛院士相比是“小”字辈,而曾经与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有的年老体弱,有的则已经故去。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满目疮痍的历史,眼前仿佛又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他们为新中国每一门学科夯实基础不遗余力;他们从未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却装满了祖国的利益。
作为后辈,我们除了继承他们的衣钵、继续发展学科体系,让那些历尽艰难建立起来的学科发展壮大,还要通过老一辈科学家的一次次讲述,牢记这段历史。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关于口述史的采访中,有位老师谈到,亲身走过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那些鲜活的经历不应该被遗忘,所以整理、记录口述史显得尤为重要。老人们口中所述的不仅是不应被遗忘的历史,更有那些值得被铭记的人物。
时间的车轮从未停止,它留下的车辙或深或浅,有些人被不断提起,有些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让那些像陈焕镛一样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不断被提及、被颂扬,成为后辈学习的楷模,成为时刻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的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11-05 第4版 人物)